“熊先生在家吗?我从台北飞来,只想问一句话。”2004年10月的一天中午,门铃骤响,北京阜成门外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,老人正靠在藤椅上小憩。来人态度恭谨,却拒绝报出姓名,只推说“他老人家一看名片就明白”。熊蕾有些狐疑纯旭配资,仍将客人领进屋内等候。二十分钟后,推门而入,看见名片上的三个篆体大字——“为真、为善、为美”,眉尖微动,只淡淡吐出一句:“原来是胡先生的小女儿。”

尴尬的客套只维持了片刻。胡为美开门见山:“父亲在台北病榻前常念叨您。我想知道,大陆究竟如何看他?”熊向晖抬头,目光落在窗外干枯的梧桐枝,良久,只抛出一句:“去读《周恩来统战文选》吧,那里有对他的全部期待。”除此之外,再无解释。这句似答非答的话,为三十分钟的会面画上句号,却引出一段长达七十年的复杂往事。
1937年冬,长沙临大青年自愿组建战地服务团北上。周恩来在汉口得知这一动向后,点将般圈出一个名字:熊向晖。此人出身书香,记忆力惊人,既懂马克思,又能背诵《总理遗嘱》,“送他去那里,最合适”。命令很简单——靠近胡宗南、摸清西北第一军动向,同时尽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。熊向晖明白,这是一条“不归路”,却欣然应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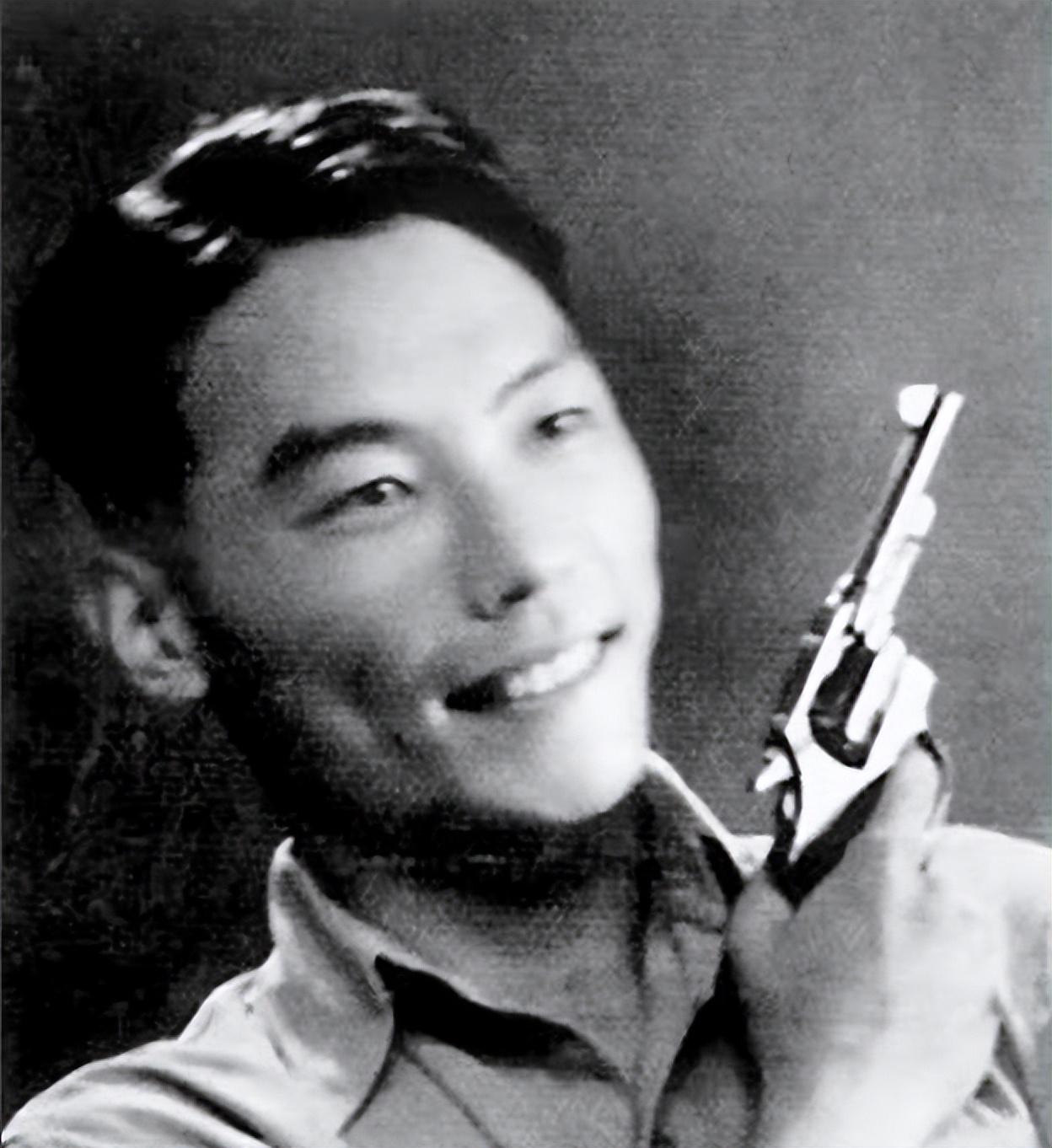
第一次与胡宗南接触,场面并不热烈:会议室里上百名青年依次起立答“有”。熊向晖偏偏举手而不站,报上姓名后加一句“愿投身国民革命”。这一细节纯旭配资,让素以“谨慎多疑”著称的胡宗南抬眼多看了三秒。当他追问“何为革命”时,熊向晖从容引用孙中山“驱除鞑虏”之语。三个回合下来,胡宗南在名册旁连画四圈。旁人不知,那四个圈意味着“重点考察对象”。
留在胡部的第一年,熊向晖被安排去黄埔七分校。胡宗南的算盘是“先洗脑再提拔”,而熊向晖的算盘则是“多学一分,日后多挡一枪”。在分校课堂,熊向晖白天练队列、析战例,夜晚默背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六个月后,他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,典礼上代表全体学员致辞。胡宗南当场表示:“随我西安任侍从副官。”这一步,将熊向晖送入核心机要圈。

真正的考验发生在1943年。那年春,蒋介石密电胡宗南,要求六月底前完成“陕甘宁肃清计划”。电报用的是最严密的密码体系,转到西安时只剩手写译本两份。其一,由熊向晖递送胡宗南签阅。夜深人静,他默记全部字段,凌晨三点化整为零烧成灰烬。第二天,延安收到加急报告,中央军委的批注只有一句:“速调兵,边打边谈,务求拖住”。拖字诀能否奏效,全系于情报源是否暴露。

蒋军部队已在同蒲路沿线集结。6月14日,朱德总司令主动向胡宗南发出公开电,指责其“违背抗日大义”。这封电报恰由熊向晖亲手呈递。当看到其中具体兵力部署与自己秘电如出一辙时,胡宗南脸色铁青,脱口一句:“是谁泄的密?”房内鸦雀无声。熊向晖主动请缨,“拟列清单逐一隔离审查,包括我自己。”如此置身险境,胡宗南反倒犹豫纯旭配资,沉吟片刻后说:“再议。”三日后,他电请蒋介石暂停行动,并以“避免国际侧目”为由获准收兵。一次可能改写历史走向的闪击战,就此哑火。毛泽东随后在延安枣园小院评价:“这个年轻人,抵得上几个师。”
抗战胜利后,胡宗南晋衔上将。西安行辕里灯火通明,他豪气万丈地对熊向晖说:“去美国念战略吧,学成回来帮我收复西北。”然而此时国共局势已山雨欲来。1946年冬,熊向晖被紧急召回西安,再次绘制“攻略延安草图”。他依旧把全文背下、抄录、传递。一张张密纸像指路的夜航灯,为陕北解放军赢得机动空间。1947年毛泽东主动撤出延安后,彭德怀在麻黄梁反手一击,胡宗南的西北劲旅元气大伤。蒋介石暗骂“养虎为患”,而胡宗南却更倚重熊向晖——讽刺的是,他把最大的破绽当成了最信赖的纽扣。

同年秋,保密局在上海逮捕王石坚,熊向晖身份彻底暴露。胡宗南接到电报,当场跌坐椅上,喃喃自语:“天下竟有此事。”但他没将此情报告蒋介石,只悄悄停了熊向晖的公费。再后来,解放战争进入尾声,胡宗南在渭水河畔节节败退,被拔掉西北王的羽翼,拖着一身病痛去了台湾。多年后,他偶尔还念叨:“若当初听了周副委员长的话就好了。”只是这句带着悔意的自白,无人可以佐证。
再将镜头拉回2004年,北京的冬阳懒懒地洒在窗台。胡为美离开前,忍不住追问:“您对父亲就没有只字片语的评价吗?”熊向晖摇头:“历史自会说话,我个人说再多,也只是枝节。”这番平静背后,或许隐藏着复杂的情感:敌我之间的较量,终点并非“恨”,而是“理解”。然而理解不等同于宽恕,也不意味着抹去责任。胡宗南在关键抉择里,没有站在民族最需要的那一边,评价如何,读者自可判断。

临别时,熊向晖起身相送,右手微举,如当年在武汉会场那样,算是对旧日上司的最后礼节。胡为美轻声道谢,脚步轻而急。楼道里只余老人低低一叹:“世事翻覆,终究一梦。”
尚红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